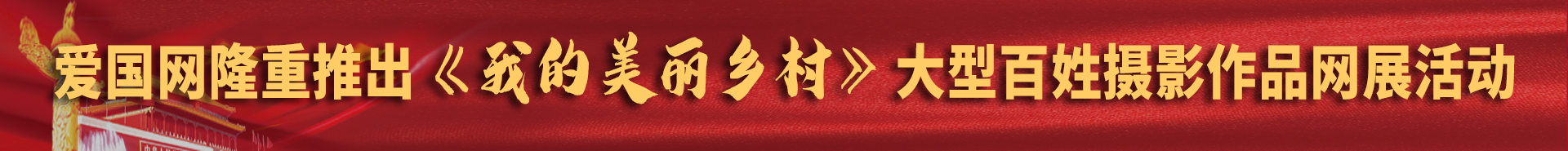忆武师中文系兼职教授郭锡良先生在武师的几件事(二)
我1983年留校任教,1986年在职考上湖北大学研究生,是湖北大学语言学方向最先招收的硕士研究生。郭先生和唐作藩先生是湖北大学的兼职教授,导师组由郭锡良、唐作藩、祝敏彻、刘宋川四位老师担任。郭先生于1986年下半年先后给我们讲《说文解字研读》和《马氏文通研读》两门课,集中授课,时间好像是一个月。我跟郭先生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。
八十年代的初中期是读书治学的黄金时期。自由探讨的学术风气很盛,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,但有些缺乏必要的检验。当时的我无疑是这些思潮的追随者。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必然现象。凡事都既有利,也有弊。当时的那种学术氛围,也有利有弊。那时我主要考虑利的一面,考虑到要多吸取知识营养,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方面的书;没有意识到,宇宙无穷,知识如海,人生有涯,任何人都不可能样样精通,炼成火眼金睛,做出科学检验,分出良莠;也没有意识到,按照这种办法去治学,必然会没有根基,浅尝辄止,泛滥无归。
我隔三差五往书店跑,了解出版信息,买了不少专业之外的西方学术思潮的书。即使到外面出差,也要到各地的书店去看看,生怕漏掉大家经常提起的我感兴趣的著作,也生怕我的学术赶不上趟。说到底,还是学术研究的自信心不足,自主性不强。这时候,除了宋川师,郭先生也是对我当头棒喝的最重要的导师。
我那时还是将学习重点放在语言学,特别是古汉语上面,以为这样就有点有面,不至落伍。其实,这个认识还是粗浅的,更多地是个托辞。没有想明白:点和面在学习中的比例各占多少?人们说,学术研究应是金字塔形的,底座的基础要宽厚,越到顶部越尖;治学越到后面,越要做窄而深的研究。从事汉语史研究,总有一天要使自己的研究领域变窄。这个时间的分界线在哪里?我这个粗浅的认识回避了不该回避的问题,因为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学术走向。我现在想,分界线一般应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:从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开始,就要求学生做窄而深的研究;如果还泛滥无归,就不可能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。博士研究生阶段,必须有侧重。有的学校,课程开设不太完备,学生经过自身的努力,考上博士生;但是,一般来说,这些位博士同学还得继续加固自学得来的知识,他或她还必须在入学伊始,赶快去弥补自己的缺陷,以免将来写论文捉襟见肘。
郭先生和刘宋川先生都发现我那时将阅读的面铺得太开。郭先生给湖北大学研究生授课,认真地跟我谈起今后的学术主攻方向。他说,他开始读研究生时,一直喜欢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,甚至还写过小说,是王力先生将他吸引到汉语史上来;王先生治学领域很宽,但一段时间有一个侧重点,不面面俱到,值得我们学习。由于王先生有侧重点,因此很多问题研究得很细致;善于小题大做,挖掘很深。这都跟王先生有明确的主攻方向有关。郭先生告诫我:研究的面不能铺得太开,一定要将看书的重点缩小到汉语史上来。汉语史领域本身范围也很宽,还得有侧重。现在搞语法史的年轻人很多,搞语音史的很少,武汉地区尤其是这样。你就侧重搞语音史吧。
郭先生要我侧重语音史,还跟我的一项学习经历有关。1985年春季的这个学期,中国音韵学会在华中工学院(今华中科技大学)办了第三期讲习班。我由湖北大学委派,自始至终参加这个班的学习,收获颇丰。李新魁教授讲《等韵学》,发了一个叫做《广韵韵谱》的表格,让学员填写,首先得系联《广韵》反切上下字。为了学习《广韵》和等韵,我利用大半年业余时间,认认真真填写了两遍。这种学习程序,对学习和研究中古音、等韵学很管用。我曾将第二遍系联的表格送呈郭先生斧正,得到充分肯定。我自己也深知,填写表格,使我的音韵学水平上了高高的一层台阶。郭先生让我将侧重点集中在语音史上,是考虑到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积累。
郭先生一席话,明确了我的主攻方向,后来我就将学习和研究重点集中在汉语语音史上了。现在看来,先生这一次谈话对我确定治学方向是一个极大的推力。
忆武师中文系兼职教授郭锡良先生在武师的几件事(三)
郭先生给研究生讲课,起先是在他老下榻的湖北大学招待所。主要由他讲,边讲边问我们一些问题。我记得他的《说文解字研读》的讲义是手写在一个很小的笔记本上,可能16开都不到,正文写满了,天头地脚也加注了不少内容。授课内容跟外面讲《说文解字》的书有不少不同的地方,主要是他加进去了一些现代语言学的元素,别有天地。
湖北大学部分师生和进修教师听说郭先生给我们研究生授课,联系中文系,咨询他能否让他们也旁听一下。系里征求郭先生意见,他答应了。于是,郭先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决定改在大教室。
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,《说文解字研读》快讲完,接着要讲《马氏文通研读》。讲完《说文解字研读》最后一节课,郭先生说:下个星期讲《马氏文通研读》,地点不在这里,在教室,有一些旁听的师生和进修教师。我讲完开场白,就读《马氏文通》的两篇《序》,分两次读。这两次课,由孙玉文主讲,我和旁听的人提问,我再来补充。
当时的治学条件远赶不上今天,我手头没有其他关于《马氏文通》第一篇《序》阅读的参考资料。回宿舍后,不敢怠慢,抓紧时间备课,连做带查,仿照平时讲解《古代汉语》文选的惯例,先将第一篇《序》作了认真的串讲,自以为这下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。
轮到我讲解《序》,郭先生的提问大出我意料。《序》中有:“欧阳永叔曰:‘《尔雅》出于汉世,正名物讲说资之,于是有训诂之学;许慎作《说文》,于是有偏旁之学;篆隶古文,为体各异,于是有字书之学;五声异律,清浊相生,而孙炎始作字音,于是有音韵之学。’”我当时只是疏通文意,对文意经过仔细斟酌,想来可能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时候,郭先生却打断了我,提了这么几个问题:(一)“欧阳永叔”是谁?(二)《马氏文通》所引“欧阳永叔”的这些话出自何处?(三)《马氏文通》引用时有没有改动?
第一个问题容易解决,二三两个问题我始料未及,郭先生等于出了我一个洋相。面对上百号旁听的学者,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没有查,不知道。郭先生接着问旁听的学者,有谁知道。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。
郭先生然后说:我们读已有的学术著作,这样的基本问题必须搞清楚,不能囫囵吞枣。光疏通原文,还不能说真正读懂人家。欧阳修的这些话见于他的《文忠集》卷一二四《崇文总目叙释·小学类》,原文作:“《尔雅》出于汉世,正名命物,讲说者资之,于是有训诂之学;文字之兴,随世转易,务趋便省,久后乃或亡其本,《三苍》之说始志字法,而许慎作《说文》,于是有偏旁之学;五声异律,清浊相生,而孙炎始作字音,于是有音韵之学;篆隶古文,为体各异,秦汉以来,学者务极其能,于是有字书之学。”《马氏文通》引欧阳修的话,有调整,有删改,大致意思没有改变。
这样的问题,今天有互联网的优势,比较容易解决,但当时却没有今天的查考条件。郭先生说,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他曾经在北大图书馆泡了大半天,才查到出处。看来郭先生读书十分细致。他语重心长地说,要想精读一部作品,对于它所引的每一条材料,都必须加以核对,切实理解,不能马虎过去。
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,影响到我今后的精读,那次授课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。这以后,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精读,也经常思考精读的意义。只有这样读书,大到一本书的切实贡献,小到它的字词句,言外之意,起承转合,甚至对人家所引用的每一则材料都不放过,才能深入体会人家,真正读进去,做到虚心涵泳。我曾经在几次演讲中明确表示:阅读著作,方能写出著作;精读经典,方能创造经典。这有我的经验教训。我们今天创造的经典不多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缺乏对一本书精读的功夫。
一个学人,在求学的一些关键时刻,要想登上一层新的台阶,不是一件易事。如果没有新的启发点,学人们往往会原地踏步,做一个马马虎虎先生;只有尽早跨过这一步,进入新境界,才能看到一片新天地。光靠自己的体悟,不容易收到这种精读的成效。任何个人,都有惰性、惯性,要想登上新台阶,除了要灵感,还要吃苦,要磨死一层皮。这时候,需要有过来人及时提醒,当头棒喝。这种提醒,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,因为有的学问大家偶尔会在他们著作中提出这种精读要求,或者在他们的研究实际中体现出来。光这个还不够,还要求求学者碰巧能看到,愿意真正实行。最亲切、最严厉的提醒和忠告,是你的导师,针对你的软肋,抓住你精读中必须要越过的关键障碍,就最具体问题,毫不客气地对你当面提出如何精读的要求,让你露出怯来,让你刻骨铭心,让你一辈子受用。
清代江永和他的弟子戴震都主张为学要做到淹博难、识断难、精审难,要做到后面这两难,需要精读经典;精读经典,最有效率的做法,就是郭先生在讲授《马氏文通研读》课程时,要我们怎样弄懂马建忠引用欧阳修那些话时的那种做法。这种做法很朴素,但最行之有效。郭先生通过具体阅读进程提出的问题、提出的阅读程序、解决问题的途径,等等,都是很微观的。但是这些具体要求,却是精读经典的最具穿透力的要求。
这种精读经典,我后来都努力贯彻执行,并向我的学生传授。在目前这个学风浮躁的时代,这种稳扎稳打的精读法,最值得吸取。郭先生所谈这种精读要求,既是对前辈学者精读方法的继承,也是他读书经验的实践性总结。我想,我将这件事写出来,对后辈读书可能会提供一点切实的帮助。